十六、日本女人为何要上街游行——姓名与法律规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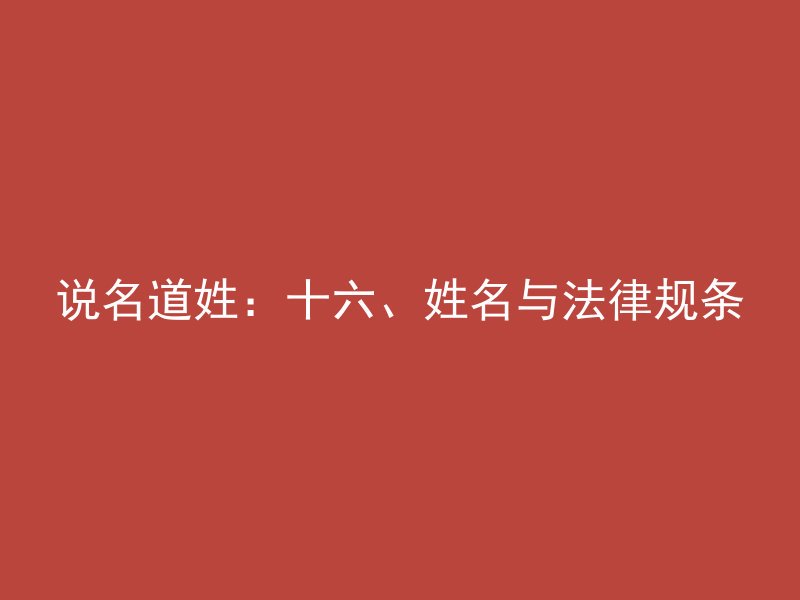
用一则新华社的消息作开篇语:
“大约20名日本女性议员11日(2001年5月11日)上书日本法务大臣森山真弓,要求对结婚夫妇只能使用同一个姓氏的现行法律作出修改。这些女性议员的行动代表了不少日本妇女渴望在婚后保持独立性的呼声。
日本现行的《民事法》规定,新婚夫妇在注册登记时,必须在两个人的姓氏中选择一个作为新组建家庭的姓氏。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妇女在婚后都放弃了自己的娘家姓氏,改随夫姓。如果女方不愿意改随夫姓而坚持自己的姓氏,那么她本人将遇到无穷无尽的麻烦,例如因难以证实身份而无法购买机票、无法接收信件,夫妇两人的孩子也将在法律上被视作‘婚外子女’而受到多种歧视,其中包括无法正常地享有继承权。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妇女不愿在婚后改随夫姓。五年前,日本政府的一个顾问小组就曾提出过修改《民事法》中相关条款的建议,其内容包括允许婚后双方各自保留原有的姓氏,并取消“婚外子女”的歧视性政策。该提议后来因遭到执政党自民党的反对而被弃用。
如今,日本国内又掀起新的妇女独立浪潮,要求修改《民事法》有关婚后姓氏使用条款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20多名日本女议员共同起草了一份修改《民事法》的草案,提出要保障婚后使用娘家姓氏的日本妇女不被剥夺应有的权利。这份草案已于早些时候送交了日本国会参众两院。
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姓名又是什么?简言之,姓名只是代表个人的语言符号。
那么,庄严的法律又与朴素的姓名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连作者自己也曾迷惑过。不过,博览大量的法律和姓名书籍后,作者不得不得出如下一个结论:同法律规条的无孔不入一样,姓名本身也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他俩不由自主地碰在一起的机会实在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鉴于姓名与法律彼此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撰此文时,作者只得借用归纳分析理论的“层层剥离”手法,从小范围到大领域,从外部交叉到内部聚合,简要析之。
姓名与法律的交叉点上有两个重要议题值得深究:一是法律条令制约和促进姓名的发展演变;二是姓名反过来以其特别的方式服务于法制法规。
姓名之受制于法,中外有别。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封建皇权史的演义和变更,是“联即国家”的八治统治手段的徘徊和重构。西方的情况则迥乎不同,虽也步入过人治的荆林,但毕竟法治观念和法制体系成形较早,发展亦见熟练。这种区别在姓名系统中也有明显的界定。
掘文就以这种区别为契机,先将姓名受制于法这一论题分中外两种情况予以阐述。国外姓名的发展要比中国迟去几千年,大量出现且达到多数人有名有姓的地步不过是中世纪中期以后的事。彼时,从法的观念上看,姓名仅作为解决财产所有权和实施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还显得不十分重要,但就姓名学本身来说,争先涌现的教名则为姓名系统充实了一支繁衍猖厥的生力军。
事实上,由于西方流行的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教会的各种立法和规定,具有法律同样的约束效果,因而把它作姓名法的“始作俑者”也是不十分过分的。例如教名的选择,必须在《圣经》、《古兰经》或教会历法的范围内;再例如,1563年无主教开会宣布:在洗礼时,如果父母坚持给婴儿另取他名,应取得天主教神甫的同意,但要冠以圣徒名作为“第二或第三洗礼名”等等,教会的这些清规戒律,对姓名的选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真正出现关于姓名的立法,是在19世纪前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播、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的出现、农村人口的增长、征兵纳税以及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口迁徙的发展,姓名作为人的代号在社会生活中愈来愈重要,另一方面,法律的日臻完备也使其触角能自由畅通地伸入姓名领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姓名与法律终于在上世纪初彼此伸出了沟通和联姻的双手。
国外关于姓名的立法有两种情况,一是本国的政府的立法,二是外国强权的挟制。
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名出乎政”的国家。日本关于姓名的立法源自宫庭。公元810年,第54代天皇仁明天皇即位后,对于御名的授予开始实施新的规定:御名必须由两个佳字组成。所谓佳字,就是由文章博士等著名文人和宫廷大臣们精心排选出的吉祥字,如堀河天皇的御名是“善仁”,后来,明治天皇对“仁”字特别亲昧,专下圣旨,规定所有皇太子名的后面一字都必须用“仁”字,所有公主名的后一个字则以“子”字为宜。例如大正天皇的御名是嘉仁;当今天皇的御名是裕仁等,即是照章办事。
当日本天皇“仁”字风靡时,除贵族有姓有名外,日本的平民百姓还只是有名无姓。明治维新后,为了方便管理,日本政府才颁布了户籍法,命令全国平民“必须人人有姓氏”。并且美其名曰此乃“日本国民的一种义务”。大概是逆反心理作崇,百姓们并不受宠若惊,大部分人无动于衷,后来政府三令五申,人们才开始翻书查史,寻找佳姓,许多人实在找不出特别好的姓氏,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了神官手中吉祥威力的标志——铃木,这么一来形成了一种戏剧效果,铃木成为日本当今最大的姓。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催促太紧,人们饥不择食,看见什么中意的东西,就信手拈来,取以为姓:有以西村、岗村之类的村庄取姓者,有以山下、山本、渡边等地名为姓者,或以白鸟、小熊之类的动物作姓,一时间姓氏大乱,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虫鱼;从职业住所到宗教信仰、从自然现象到思想意识,各种各样的姓氏散布东羸。如高杉、西园寺、服部、大庭、鸟居等等,据当时的史官统计,几千万日民享有二十多万种姓氏,真是蔚为壮观。
为了消除紊乱、精简姓氏,鉴于日本人名中汉字使用涣乱成灾,1946年,日本政府对日语中的几万汉字进行了改革和限制,公布了1850个当用汉字,连同此后补充的92个作为新生婴儿取名的选择,否则政府不予注册户籍。这一改革收效显著,日本姓名的发展从此逐渐走向集中和精练。
日本政府在1898年颁布的户籍法中规定:每户都要有固定姓氏,子承父姓,妻从夫姓,分家后仍用原姓,不得任意更改,日本的夫妻同姓现象自此始矣!不少妇女同志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大男子主义作怪,遂自发组成“反对结婚改姓会”,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企改变这一局面,后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本文篇首那则消息看来,男女平等的口号还得继续喊下去。
西方关于姓氏的立法始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9世纪未,法国大革命倡导自由之风,姓名系统亦坐上顺风船,人人皆以别出心裁的名字自傲,各种怪诞名充斥街衢,第一共和国掌权后,1803年,新政府制订一份专门的姓名法令,将起名的来源限于历史人物和各种历法,并规定公民起名之后不但不能自行改姓,就是改名也须正当理由,并提交民事法庭审议批准,换姓还须由国家元首在官方报纸上发布更换姓氏的法令,一年之后,换姓者才能要求民事法庭批准使用新姓,由于换姓改名得之不易,那些觉得现名不佳者大多私下起个名字,在亲朋好友中叫着过过瘾,到了官方场合又恢复原名。
1804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出台,又给灾难深重的姓名系统套上了一道紧箍咒:法典不仅规定每个法国公民都有义务把家系名称的姓在本族中代代相传,而且还要求当时处于法国支配下的邻近各国照办,从此,限制取姓,用姓的各种法规在欧洲各国纷纷推出。
法国以后,姓名立法较早且条文完备的当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劳兰。不过这已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了。1921年,芬兰政府颁布《姓名法》,严正声明公民的姓名受法律保护,并由专门机构管理姓名档案,监督姓的使用。若发现非法使用他人的姓,可向法庭起诉。若要改变姓名或增减自己的名字,必须向当局提出书面申请,经核准后并在地方报纸上声明,才能向户籍机关登记备案,方始生效。
土耳其姓名立法是和其它改革措施一起出笼的。1934年11月24日,刚刚享受到革命胜利果实滋味的凯末尔政权通过大国民议会实施了《取姓法》,法案公布之日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带有宗教封建色彩的尊号和称号一律作废,并实行新的称谓方式:巴伊和巴杨,即先生(Bay)和小姐(Bayan),巴伊、巴杨和姓一起使用,放在姓氏之前,如Bay A Kyol 或Bayan Akyol ,即巴伊阿克约尔,巴杨阿克约尔。
土耳其人原来没姓,《取姓法》却规定每个土耳其人必须有姓,为了让公民取姓方便,政府提供一份单子,让人从中挑姓,如厄兹蒂尔克(真正的土耳其人)、切廷蒂尔克(严肃的土耳其人)、申蒂尔克(高兴的土耳其人)、阿克约尔(一路平安)等等,尽管如此,土耳其人的用姓还是禁不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以药济师、渔夫,姆拉格人等职业、出生地为姓,有以父名或父亲职业为姓的。如姓“皇斯曼拉加的儿子”(屠夫或肉铺掌框柜的独儿子)。此外,重大的历史事件、神话故事,动物,绰号,一些独特的词等亦被取以为姓。如当今土耳其最著名的作家阿齐兹·纳辛(Azziz Nesin)的姓“纳辛”土耳其语意“你是谁”这就象中国公民姓山芋、黑驴、别碰我、母夜叉一样实乃姓名学中一绝。
各国政府关于姓名的立法基本上是严谨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如只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就有100万人使用安德逊,约翰逊,卡尔逊三个姓,而且有300万人的名字只局限于六个男名和六个女名。同姓名现象给政府工作带来麻烦,政府于是采取“大棒加黄油”政策,下令鼓励百姓改名易姓,并规定给予一定报酬,还设计了不少音节优美的姓氏供人们参考。与此相反,荷兰人要改姓则要向政府及女王申请,还须缴纳250荷兰盾,其邻国比利时招术更绝,谁要改名,得交“改名税”。更有甚者,冰岛在1925年6月27日通过《姓名法》,禁止人们用姓,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自由”。
法律本身是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强权的压制,往往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征服和被征服的历史上,往往会产生种种畸形的,强加于被征服国的法律,人名文化中的外国强权的压制,也有其明显的烙印。
最能反映政治强权对文化冲突和交融的例子是犹太人的人名系统。犹太人名可谓历尽沧桑,伤痕累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股排犹反犹浪潮,1787年,奥皇下令加里西亚和布哥维那的犹太人采用固定的姓,并向当局登记。不久,俄国沙皇和拿破仑也随之效法,下令境内所有犹太人在限制期内选好固定的姓。所谓固定的姓,就是在限定范围内的姓氏,如匈牙利的犹太人就只能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姓。更有不少国家强加给犹太人一些带有侮辱色彩的姓。如“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等,在权力强权面前,犹太人不得不屈服地依从了。
二战时期,犹太人又成了砧板上之肉坯,任人宰割。1938年8月17日,德国纳粹当局下令,禁止犹太人使用非犹太人的姓名,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名和91个女名,规定要求1939年1月1日前,犹太人必须用新姓名到地方当局登记,此后所有活动都以新名为准,否则无效。继纳粹希特勒之法令后,欧洲的纳粹傀儡竞相仿尤。法国维希当局于1942年3月通令禁止犹太人用非犹太姓名。同年7月,挪威吉斯林政府也下令禁止犹太人用与挪威语言相通的词作姓名。这些反动法令直到1948年犹太历5月14日以色列国成立,大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后才基本废止了。
无独有偶,太平洋上之岛国菲律宾也曾遭到同样之命运。1521年3月16日,探险家麦哲伦代表葡萄牙人登上了菲律宾。十七世纪以后,江山易主,西班牙人成了群岛的主宰。1849年11月11日西班牙驻菲总督克拉维里亚颁布一道命令,强迫所有的菲律宾人改用西班牙姓,法令上附有数以千计的从马德里姓名地址录和旅游日誌里抄来的西班牙姓,供菲律宾人按地区挨村挨户地选用,现在菲律宾常常一个镇或一个村的人大都使用同一个字母起首的西班牙姓,便是殖民主义文化的镜像。
其实,何止犹太人和菲律宾人如此。有殖民主义和战争强权压制的民族,姓名系统基本上都打上了铁铸的烙印。老挝人使用姓迟至于1943年7月28日,就是由于法国殖民主义者驻印度支那联帮总督下令规定每人须有名有姓才开始出现的。目前,许多非洲黑人姓白人的姓,也是殖民主义大棒政策下的产物。
中国是姓名发展最早、最完备的民族,又是封建统治最娴熟、最顽固的国度。人治和礼治的普通和规范化的应用使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毫无余地沐浴在“三纲五常”的氛围之中,反映在人名学系统里,从姓氏的产生、名、字的来源到讳名禁忌、谥号单名的流行无一不浸透着封建礼法的精髓。
中国人的姓名,源于上古,几千年代代相传,繁衍发展,源远流长,纵贯如一。比起其它民族仓促上马,病急乱投医要丰富、有趣得多。单是姓名与法律条令这一点,华夏姓名的“法”、“礼”就大大的丰富、具体于其他民族。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诏令可谓是法中之法了,最能反映姓名的法制态度的是天子、皇帝赐给臣民姓氏,即赐姓,它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和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是我国姓氏来源的组成部分之一。
赐姓之制,远在氏族社会神话传说时代就有了。《国语·周语(下)》说:“唯有嘉力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大禹就因治水安民有功,故“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妣,氏曰有夏。”关于赐姓之制,《左传》有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上古三代,天子令诸侯,诸侯命卿大夫,许多姓氏之产生都要经过赐的手段。
赐姓之风,也经过“起承转合”的历程。上古三代所谓赐姓,都是在原本没有姓氏的情况下通过天子之命而产生问世的。如舜时有一个叫董父的人,擅养龙,许多龙都飞到他的身边,舜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当即赐董父姓豢龙。后来夏朝出一个刘累,跟豢龙氏学习养龙,十分卖力地为帝孔甲养龙,孔甲见其技艺精良,就赐他为御龙氏。周朝,周穆王之庞妃盛姬死后,穆王为表示衰痛,就赐她的后代姓痛。
秦汉以后的赐姓有别于上古。多为最高统治者出于自己的意志,将别人已有的姓抹掉,换成另一个姓。一般情况下,新换的姓是早有的姓氏,这个时代的赐姓还有一大特征,即赐姓的褒贬观念十分强烈。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姓是最为尊贵的。出于褒赏,拢络等目的,各朝皇帝赐给臣属的姓大都是“国姓”,即皇帝的姓。
汉朝刘氏登上龙庭后,不知是为了安抚,还是出于炫耀,就曾把与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项羽后裔全部赐姓刘。李姓唐朝则将开国治政的文臣武将如徐世勣,安抱玉,胡大恩,郭子仪等赐姓李。对少数民族归顺的臣属亦是如此。沙陀族的宋邪赤心就被赐以国姓,改姓名为李国昌,他的后代袭用李姓,在五代时,其孙李存勖就利用这个“李”姓建立后唐,即后唐庄宗。赵宋王朝时,朝迁所赐之姓都以赵为主,到了明朝朱元璋坐天下,朱姓又被朝廷作为拢络人心的工具。明末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就因为“相貌堂堂,屡建奇勋”而被赐姓朱,至今,东南治海与日本人都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与赐姓示庞,惠恩相反,统治者还把赐姓作为最严厉的手段,责令政敌改姓。汉高祖刘邦得秦天下,开国功臣、淮南王英布反叛未遂,刘邦嫌诛斩英布不足解恨,查宗问族得知英少年时曾为江洋大盗,受过黥刑,就赐其子孙姓“黥”。隋炀帝的大臣杨玄威趁隋第二次挥兵东征高丽时,起兵暴乱,后兵败被杀,枭首示众,隋炀帝效法前人,赐杨玄威后人改姓枭。
示惩的赐姓往往含有凶恶、不祥之意,而被赐者则多半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赐其姓无疑是一种惬意的述志方式。虺、蟒、蝮均是青蛇、毒虫之属;蛸,章鱼也,这些丑恶的东西就分别被唐、北齐当政者赐给判乱未遂的萧响、武维良、李员、李冲诸公。赐姓改名是武则天发泄私愤、攻谄政敌的绝招。她曾改“叛臣”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成斩,突厥可汗默啜为斩啜。“蝮”字就是她为了表示对自己两个叔父武维良与武怀远的厌恶之情而强赐给他们的。为笼络人心,武则天还把辅佐她的臣属集体赐姓武,并将其面首冯小宝改名薛怀义,武氏可算历史上赐姓名最多的君王了。
诸朝代的皇帝赐姓,并不只局限于国姓和丑性,也有皇帝一时兴起赐予的,这样的赐姓往往很幽默滑稽。东普明帝时,殿前都尉兼宫延讲官余讽常与明帝议论朝政。一次,明帝心血来潮,忽然对余讽说“余者我也,讽者讥也,卿为此名,欲为联之敌乎?”当赐将其“余”姓出头的一竖抽掉,赐姓“佘”。余讽回家后,想到自己竟为皇上所忌,恐怖非常,干脆改名“佘顽”,据说“佘”姓即由此而来。
洪武十七年,元朝工部尚书丑驴附朱明王朝,朱元璋嫌其名字太过鄙俗,当即赐其姓“李”,改其名曰“李贤”。南唐皇帝一次看见一位叫哀榆的大臣,觉得这个“哀”字在庆贺时不吉利,灵机一动,在“哀”字中间插了一杆,赐其姓衷。如此种种,皆是封建帝王为所欲为的话证。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朕即国家”,被皇上赐予国姓的人,不光图个虚名,还能赚得实惠。刘汉王朝就曾明文规定,凡诸刘全家免一切徭役,且非刘姓不得封王。于是十多万刘姓皇民都得以享受中级以上官员的待遇。至于那些被赐改姓的政敌,当然也得有所实际“表示”。朱明王朝时,朱元璋就把政敌陈友琼及其主要部属钱、林、袁、孙等姓后裔贬在新安江上为渔民,并不准他们上岸居住,不准入学读书,不准参加科举,甚至不准穿鞋子,真正无所不用其极了。
另外,不少皇帝还强行颁布姓氏高低贵贱排列表,以示皇族高人一等,前文已述,在此就免谈了。
封建法规除了对姓氏的源起和发展大施淫威外,对于平名百姓的起名,也丝毫不放过,战国专制度的主宰者制定了专门的命名法,凭其主观臆想做准绳,叫大家都服从,符合标准的便合法、文雅,不合标准的就不合法,粗俗。关于这种情况的文字,《左传》有专文记载。
桓公大年九月丁卯日,桓公的太子出生,桓公问其大夫申 ,应该怎样命名,申繻便陈述命名须遵循五种方法、六项规条的礼制。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文,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这是讲的命名的五种方法。桓公的太子因与桓公同生日,就依了“取于父为类”一条,命名曰“同”。接下来,申儒又讲了命名的六项规条,云:“不以国,以国则废名;不以官,以官则废职;不以山川,以山川则废主;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以畜牲则废祀;不以器帛,以器帛则废礼。”
六项规条,即避讳之滥殇。后来,关于避讯的各种奇形怪壮的规定浩浩荡荡席卷整个人名学系统,成为中国人名学受制法的最佳明证。鉴于前文已述,在此也来个避讳吧。“五法六规”和讳兴之后,关于人名的取法,历朝历代的君主又都有各自的“御旨”。《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曾诏令禁二名。他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五莽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制铜印三颗,与乃舅合谋欲早承祖业,事发,宗自杀,为了表示严正公明,王莽鉴于“宗本名会宗”,乃罚其“以制作去二名,令复其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以此说明去二名,是朝延的庞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如此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单名之风便刮遍神洲,以至以后汉魏三百年,几乎人人皆单名,《后汉书》和《三国演义》里的人名,单名占了98%。文武显要,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黄盖、孙权、曹操等;清一色的是单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亦皆单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单名限字太少,复名颇多,与王莽同时代就另有一个大将军叫王莽。王莽若知道其“圣讳”被犯,不知又该作何举动。
王莽以后,新招又出现在宋朝。寓意有王霸思想的字眼,禁止取之为名。《容斋随笔》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卫上达,方天伍,金圣求诸公只得改名为毛友、卫仲达,方大伍,金应求。”若是不改名,作何处置呢?《能致斋漫录》有云:“恭覩政和中二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当时名法之严,可见一斑。
谥是华夏姓名家族的特产,它从产生,发展到演变,无一不在皇权的督护之下。谥法作为古代典章制度与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于周初,损于清末。其间虽被秦始皇以“子议父,臣议君”之名一度废止,但仍健康长寿地荣华富贵了两千多年。鉴于前文已述,作者在此不想强调谥法的繁文缛节,只想提醒一下读者,姓名与法律条令的关系中谥法是一个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最后谈谈姓氏与婚姻法。早在周代,同姓不婚即见之于法律、制度的社会规范和约定俗成的伦理准则。《韩诗外传》“周公制礼,百世不通”,规定只要是同姓,不论远近亲疏,即使相隔万代,均不得通婚。什么原因?《晋语》曰:“同姓不婚,惧不殖生”。怕近亲结合影响优生优育。根据“同姓不婚”原则:“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因此,时人订亲前,先“男女辩姓,”遵循“礼之大司”,否则就是失“礼”甚至违法。孔圣人就曾因不懂“同姓不婚”法而差点被人误解。
《论语·述而》讲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懂不懂礼,孔子说他懂礼,陈司败就对孔子的弟子埋怨孔子偏袒鲁昭公,因为昭公娶了位与昭公同姓的吴国女子,违反了“婚姻法”。孔子后来明白过来,赶紧认错,承认鲁昭公不懂礼,此事才算了结。
先秦的同姓不婚制度虽陷于严厉,但它为种族走向繁荣,维系和延续宗法制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到现在还有市场,并且“出口”到许多邻国。如朝鲜高丽王朝时期,忠烈王昛曾于1308年下令全国,禁令同姓近亲通婚。李成桂灭高丽后,援引了中国明朝《大明律》法典,对同姓婚者施以杖刑。1470年,朝鲜《经国大典》还规定,同婚异籍者也不准通婚,种种事例表明,姓氏在婚姻法中可谓重要矣!
古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姓名处处受法律钳制,它是否有反抗法律的时候呢?当然有,但却是“以德报怨”,服务于法律。象法律程序中的无记名投票、法律条文中的著作权法,违法形式中的侵犯公民名誉权等,无一不是如此。鉴于头绪太多,在此仅以著作权法作“法人”代表,简要谈谈。
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有权在作品上署真姓名、笔名或不著名。剽窃他人作品的,以自己名义发表即违反著作权法。继前几年著作权法制定后,今年元月,版权法出台,围绕此类的“名誉受损案”便接二连三地涌现,在此姑且不谈这些人所尽知的腓闻,只给那些似违法又非违法的投机之徒亮亮丑:
1991年秋冬之交,上海各大书店上柜一批武侠小说,展示了一些打版权法“擦边球”者的奇招妙术:柜台上同时出售分别署名“金唐”、“金康”、“全庸”的各类武侠小说,以种种近似“金庸”的姓名在封面上以行草书写,许多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是金庸的又一力作,纷纷解囊抢购。书店和出版社为此大赚其钱,作者本人当然更是囊中丰实,只是可怜了那些虔诚的读者,花钱买个当上,不免又对社会多了一层戒备。
此招其实不鲜,三十年代就有名巴全者作《冬》一书被人误以为是巴金自己《秋》的续书;前几年齐秦唱红后,街头巷尾又冒出了齐泰的带子。世有法律,人有诡道,法死人活,二者斗智斗勇,互有胜负是自然的,这里,只是给诸位提个醒而已。
